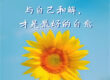深秋的夜晚,凉意浸骨。30岁的阿宇踉跄着推开家门,满身酒气像一张密不透风的网,裹住了整个屋子。母亲刚要开口问些什么,他猛地甩掉外套,径直冲进卧室,“砰”的一声重重关上房门——墙上那帧前年春节的全家福,被震得微微颤动。照片里的阿宇穿着藏青色西装,眉眼间满是意气风发,与此刻房间里那个颓丧的身影,判若两人。
母亲望着紧闭的房门,泪水无声地滑过脸颊,滴在冰凉的地板上。三天前禁毒社工家访时的话语又在耳边响起:“阿宇已经两次没按时唾检了。”还有那句“心瘾比身瘾更难戒”,像一根细刺,深深扎在她的心头,拔不出,也忘不掉。
坠落:从摄影新星到毒窟囚徒
阿宇的人生,曾是旁人眼中的“标准答案”。15岁拿下全市青少年摄影大赛三等奖,18岁考入重点大学美术系,22岁一毕业就创办了自己的摄影工作室——镜头里的他,总能捕捉到生活最鲜活的模样,可镜头外的人生,却在不知不觉中偏离了轨道。
三年前的那个雨夜,一切彻底崩塌。警方在夜店包厢里查获阿宇时,他因吸食过量海洛因而神志不清,经过紧急救治才脱离生命危险,随之而来的,是两年的强制戒毒。戒毒所的高墙外,父亲一夜白头;高墙内,阿宇在日记里狠狠写下“我恨那些所谓的朋友”,字里行间满是悔恨。
可这份悔恨,在出所那天就险些被冲淡。他刚站在戒毒所门口,昔日“毒友”阿杰的信息就弹了出来:“阿宇,今晚老地方,给你接风洗尘!”彼时,社工正提着印着“新生启航”的欢迎礼包迎上来,阿宇脸上挂着漫不经心的笑:“王社工,我保证按时报到,您放心。”那时的他以为,戒毒不过是“不再碰毒品”那么简单,却不知,心瘾的拉扯,才是真正的硬仗。
拉锯:在“配合”与“失控”间摇摆
最初的三个月,阿宇确实扮演了“完美康复者”的角色。社工随叫随到,每次唾检都准时出现在卫生院,甚至会主动聊起最近在看的摄影课程,语气里透着几分积极。社工还注意到,他的手机壳里夹着一张皱巴巴的纸条,上面是他在戒毒所写的决心书:“再碰毒品就是狗”,字迹用力到几乎划破纸张。
转折发生在第五个月。那天下午三点,本该是阿宇唾检的时间,他却迟迟未出现。社工拨通他的电话,听筒里传来KTV嘈杂的音乐声:“王社工,我陪客户应酬呢,明天一早就去补检!”挂了电话,社工望着窗外飘雨的街道,想起上周家访时阿宇母亲的担忧——最近总有辆黑色轿车深夜停在巷口,司机下车后会给阿宇递烟。
放心不下的社工,当晚就撑着伞去了阿宇家。推开门时,阿宇正戴着耳机打游戏,看见社工的瞬间,他条件反射般关掉了游戏界面。“又去应酬了?”社工指着他衣领上的烧烤油渍,话音刚落,阿宇突然提高了音量:“你们是不是在我身上装了监控?我就不能有正常社交?”
母亲端着姜茶走进来,小心翼翼地打圆场:“阿宇,你上次说想重新开摄影工作室,我和你爸都支持……”“我不需要你们管!”阿宇抓起外套就冲出门,社工追出去时,只看见他的背影消失在茫茫雨幕中。那一夜,社工在办公室翻出阿宇的成长档案,看着那些曾经闪耀的履历——摄影奖、重点大学、创业故事,再对比如今的困境,心里五味杂陈。
觉醒:在“差点复吸”的边缘悬崖勒马
三周后,阿宇主动敲开了社工办公室的门。他低着头,声音发颤:“那天晚上……我在巷口差点又碰了那个东西。阿杰说现在流行‘电子烟’,不会上瘾……”
社工没有责备他,而是指着窗外正在修剪枝叶的园艺师:“你知道戒毒最难的时候是什么吗?就像这棵香樟树,春天抽新芽时最容易遭虫蛀。戒毒成功不是终点,而是新生活的起点。”她翻开《社区康复手册》,指着“三年康复期”的红色标注:“这三年里,我们会陪你面对心瘾的每一次反扑。康复不是消除对毒品的记忆,而是帮你建立‘即使想起,也能拒绝’的心理韧劲。”
从那以后,社工为阿宇制定了更细致的康复计划。“毒友隔离计划”帮他切断与过去圈子的联系,社工还设计了应对诱惑的标准化话术,通过角色扮演模拟各种施压场景。“如果阿凯再约你去夜店,你怎么回答?”社工故意压低嗓音模仿“毒友”的语气,阿宇攥紧拳头,按照练习过无数次的台词回应:“我现在有更重要的事要做。”
重生:从摄影助理到重拾热爱
随着朋友圈逐渐“净化”,新的问题又出现了——阿宇的母亲忧心忡忡地找到社工:“他整天把自己关在房间里,连相机都不碰了。”社工明白,要让阿宇真正重启人生,一份能让他找回价值感的工作至关重要。
通过社区资源链接,社工为阿宇争取到了摄影助理的岗位。当社工把这个消息告诉阿宇时,他却激动地把简历摔在桌上,指节因用力而发白:“让我当助理?我可是拿过市级摄影奖的!”
社工捡起简历,指着上面的获奖作品《破茧》——画面里,一只蝴蝶正用裂开的茧壳编织翅膀。“这张照片告诉我,你比谁都清楚,暂时的蛰伏意味着什么。”她将工作合同推到阿宇面前:“助理只是起点,闲暇时你还可以继续参赛。记住,金子在任何角落都会发光。”阿宇盯着照片看了很久,最终签下了合同。
三个月后,阿宇拍摄的《重生》系列在社区摄影展上获奖。照片里,有雨后的新芽,有阳光下的花朵,还有社区里人们的笑脸——每一张都充满了生命力。
破茧:三年期满,与过去的自己告别
三年时光,像相机快门一样一闪而过。最后一次唾液检测时,阿宇突然开口:“以前我拍照片总喜欢调暗色调,觉得人生就像底片一样灰暗。”他摩挲着相机背带上的铜扣,眼神明亮:“现在我才明白,摄影不是记录完美瞬间,而是定格那些破茧成蝶的时刻。”
社工望着检测板上清晰的阴性结果,轻声说:“你今天拒绝的,不仅是毒品,更是过去那个被心瘾困住的自己。”阿宇举起相机,镜头里映出两人相视而笑的画面——取景框外,春日的阳光正为整个社区镀上一层温暖的金边。
如今,再有人问起那段经历,阿宇总会笑着说:“戒毒不是终点,而是重新认识自己的起点。感谢那三年里所有的‘被看见’和‘被相信’,让我终于敢说——我值得拥有更好的人生。”
青浦工作站盈浦社工点 王凤 供稿